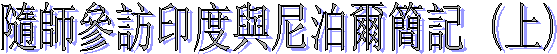
�B �� 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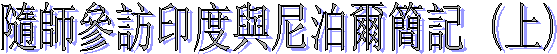
�B �� ��
�Ĥ@�� ���뢱���� �e�ۻO�X�o�f
�����L�P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ȡA�D�n�O�H�P�W�v�Դܥ[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ܥ_�L�שԹF�J
(Ladakh) �ѳX�A�P�ɨ���ìy�`�F���Ҧb�a���F�i�ĩ� (Dharamsala)
�|���@�Ǥ��i�����Ѥ͡A�]���K�쥧�y���ż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|���u�{�i�סC�ӳo�@���ԹF�J�a�Ϥ@�檺�]�t�A�D�n�O�h�~�Q�@��ɡA��^���|���b�ԹF�J�a�Ϧa��̰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 (Rtogs ldan Rinpoche)[1]
���ܳX�����k�A���~�ܯÿA��{���i�ڤ��߫��X�C��줯�i���O�h�~���n�͡Aų��Դ����i���w�h�~�����y�X�ԹF�J�A�G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ܽ��@�C�C
�ԹF�J��L�׳̥_�ݡA�ݤ���ؤ��̺��P����� (Province of Kashmire and Janmu) �A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٪��T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k�A�a�հ��m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d���ʤ��ءA�P���Ī����۷��C���a��Ʀۥj�Y�`�����üv�T�A���u�p���áv���ٸ��C��A�X�ȹC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O�C�~������ܤE�뤤���A�Ӥ��i���M�w�b�ȹC�u�}�l�e���|��U���e���C
�ڭ̤@��|�H�Ф��i���BSu�B�p��B�ڡA�f���د���|����}�ҥѥx�_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s�w�����s��Z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Ȥ��I�T�Q���_���A�g�C�p�ɪ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T�Q����F�s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i��O�s��Z���t�G�A�Z���ȥb���A�ҥH�b���W�ڭ̳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Ŷ��o��𮧡C
�ĤG��
���뢱���� �e��F�L�סA�e���F�i�ĩԡf
�o������{�p���A�D�n�O�z�L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Ѥ͡Хx�W�u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év�а���|�v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 (Mr. Atisha) ���w�ơA�ҥH�@��F�s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N���@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Ӫﱵ�ڭ̡C
�������{�~�|�Q�����A�O��|���W�K�|���n�s�w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A�t�d�z�W�K�|�b���a�u���ç��v(Tibetan Village) �Ҹg�窺���] Gyutuo Guest House�A�����T�~�A�L�w�b����¾��~�A���~�N�^����F�L�ת����x�C
�u���ç��v���s�w����Majnu-ka-tilla�A�쥻�Ȭ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L�ɪ��b�ױH�~�a�A�v���o�i�����@�ӼƤd�H�����ϡA���M�Ҧ����ؿv���ݹH���A���O�o��h�~�ӡA�L�F���]�O�C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۷��h���p���ө��B�\�U�B���]�b���C�W�K�|�����]�w�g���I���¡A�ҥ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Ƨڭ̦��b�@���~�}�i��P�����u�äک������v(Zanbhala
Hotel)�A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u�O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p�Ȫ��A�ӥB�S���N��A���O�]���ڭ̹j�ѴN�n�����h�F�i�ĩԡA�ҥH�]�N�N�N�@�U�F�C
���W�K�I�ιL���\��A�ڭ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̥��q�ܡA���i���s���W�L���Ѥ��ЧJ�]���� (Mkhas grub)�C�J�]���b�s�w�����t�@�Y�A���b�o�̤w�g���T�Q�~�F�A�O�ӥͷN�H�A�]�O�w�G�ĭ{���w�Q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˱��C�J�]��F����A�ڭ̤@�_�h�䤯�i�����t�@��B���дL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 (Brtson grub Seng ge)�A�L�N���b���ç��̡C�L�]����O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P�m�A�H�e���O��^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ño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Ǧ�A����٫U���d�ͤl�A���ߥX�����A�{����^���|�b�L�שҥX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y�A���O�ѥL�ҦL�檺�C
�L�]����S�Q�줯�i���|��M��L�a���X�A�۷���ߡA�ܼ��۪��۫ݧڭ̡C�L�M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F�@�Ǫ�p�G�쥻�b�j�[�L�x (Byang chub gling) �Ҷi�檺�k����J�q���p���A�{�w����L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Ӷi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o�ǿ�J�չ諸�u�@�C
����کM���i����L���a�U�ǮѮw���ʤ@�ǥL�ҥX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A���O��X�����N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q�w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q�w�·S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i���t�~�R�F�@�����y�k���A�dzƱa�h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˦�ǰ|������̥ΡA�ګh�t�R�F�@���ª������y�A�p��Ǧh�ǥ��� (�L�O�ĥ|�@�ˤd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̤l)�B��v�ն�
(��v����O�K�Ǥ�ڪ��̤l) ���C
���Ȥj�a�@�_����� Rab gsal Hotel �Y���\�C���ᦳ���t�d���r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Ө줯�i�����ж��V���i���б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e�A�]���ª���ۥ������\�h���~�A�L�̵L�k�P�w�A�ҥH�ӽФ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ǫ��ɡA�ګh�M�J�]�����ѫn�a�_����ѡC��ӴL�]������ͤ]�Ө줯�i���ж��A�M�ڭ̵���ѿ��CSu �h�N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ؤ��L�]������ͻP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H�@�i�ڤ��ߪ�T-shirt�A�H�ΨC�H���ʿc�Ѿi�A�H���¥L�̬���z��^���|�ǩӪk���Ұ^�m���ߤO�C
�b Zambhala Hotel �ιL²�檺���ѫ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e�ڭ̥h�f���C�I���}���F�i�ĩԪ��T���C���{���Q�G�p�ɡA���p���O�Ӧn�A���٦n���l�u���b���A�ڭ̨C�H���i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y�j�j�𮧡A���F�A�l�����ӥm�r�~�A�@���W�ٺ⥭���C
�ĤT��@���뢱����@�e�b�F�i�ĩԫ��X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B�̡ͭf
���W�C�I����F�F�i�ĩԡA�W�K�|���P�y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ڭ̡A�L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Ҧw�ƪ��A��U�ڭ̮��]���J�P�q�ʦ^�{�������Ʃy�C�ڭ̦��b Surya Hotel�A���O���a�L�פH�Ҷ}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]�ƫܤ����A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ӫK�y�C�b�ιL���\��A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Ѥͥ��赦������
(Bkra shis tshe ring) �Ө춺���A�M��ڭ̤@��H�N��L�ҥD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c�v(Animachen
Institute)�C
���赦�����ͬO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y�Ǫ̡A���~��¾��u�����ɮפ��m�Ϯ��]�v(Library of Tibetan Archives and Works)�A����öDzΤ��m�۷����x�A �o�X�~�L�M�t�~�X�����y�Ǫ̦X�զ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c�v�A�H�O�s���öDzΤ�Ƭ��ت��A�X���F�\�h�^��B�ä媺�U���dzN���y�C�L�b1998�~�ѥ[�����L�Ħw���j�ǩ��|�檺�ĤK������þǷ|ij�ɡA�ڦb
Gene Smith ���ͨ��̴��M�L���L���A���L�S���ɶ��V�L�h�бСC����L�⦸�y�X�ì��A�����쩣�i�ڤ��ߨӬݤ��i���C���i���o����F�i�ĩԡA���D�n�]�O�n�䥾����͡A�]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F�Ʀ~�ɶ��Ҽg���m�n���a��ӡn�A���ХL���չ�s��A�M��ѡu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c�v�X���C�o���Ѥ��ȸg�L�L���ԲӼf�q�A�L�]�[�J�\�h�L�Ҭ��ê������Ӥ��C�g�L�L�P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̫�Q�שw�Z��A�o���ѱN�멳�X���C
�ڤ]�Ǧ����|�V������ͽбФF�@�Ǧۤv����s�W����ư��D�A�ᦳ��ì�C������ͯu������öDzΤ�ƪ��O�s�۷����ߡA�|�Ҩӻ��A�H�e���ê��H�DzΤW�|��a�@���¦����j�A�o�غj�����Q�K�B�Q�E�@�����ɪ��Ӻֺj�A�@���u�ॴ�@�o�C�äH�ϥγo�غj�����v�۷��[�A�Ʀܨ�1959
�~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ɤ��b�ϥΡA���{�b�]�����ҥH�ά�i�B���]���A�äH�w�g���A�ϥγo�س��j�A�o�ضDzΤ]�v�����ǡC������ͻ`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ä媺������ơA�]�ܺB�n�����F�ڤ@�� copy�C���@�쪺�O�����ȱo�@���A¿�ԡE������� (Nyag bla Padma bdud
'dul, 1816-1872) �O�@��线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̡A�D�n�ͬ��b¤��a��A[2]
�b�L���ۧ@���A���@�q�U���äH���n�ϥγ��j���л|�A�L���A�̦p�G������ϥγo�ǪZ���A�{�b�o�غj�u��@�o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ͩR�A�N�ӷ|����s�B��n���Z���A�@�o�i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W�U���H�C�i���S�Hť�q�L���U�i�C
���ȧڭ̤j�a�@�_�� Tibet Hotel �Y���A�P�檺�|���F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 (Zla ba tshe ring)�A�L��q�x�W���u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év�а���|�v�զ^�ӡA��¾��y�`�F�����~��ݷs�D���A�]���L�Q�~�e�~�q�C���k�X�ӡA�ҥH�~�y���o�۷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i���M���赦�����ͦ^�h�~��Q�צ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Ʃy�A�F�˫h�a�ڭ̥h�u�ե��L�d�v���[�C
�u�ե��L�d�v(Nor bu gling
ka) ���ӬO�F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Įɪ��L�c�W�١A�{�b�F�i�ĩԫh�N���ئ����öDzΤu�����V�m���ߡA�б�ø�e�B�J��B��u���ҵ{�A�åB�]�i��L�̩Ұ����u���~�ASu �P�p��R�F�L�̩Ұ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l�A�ګh�R�F�L�̩ҥX�����ä����x�P���y�C
�^����]��ASu �Τp��^�Х𮧡A�ګh�h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c�v�䤯�i���L�̡C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b�˵����赦�����ͥѦ��b�W�K�|���ĤQ�C�@�����ڨ��̩ҭɨӪ��|�Q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n(Karma
chags med, 1613-1678)��ۥ��A�o�@�M�ѧڥh�~�h�_�ʡu�����þǬ�s���ߡv�}�|�ɡA�b�L�̪��Ϯ��]�̨��L�A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ڻ��O�b�|�t�����p�H�X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i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L�q����@�Ǹ�ơA�ڤ]���K�ݨ�@�ǩM�ڪ���s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ۧ@�A���O�m�j�d���ɵo���y�n(thugs
rje dmar khrid sems bskyed)
������ɶ��A�S��k copy�C[3]
�^���]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A�I�줯�i�����t�@��B�͡о�����إ��� (Karma chos 'phel)�A�L�O�e�����y�`�F��ij�|ij���A�{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ij���@¾�A�L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j�Ѥ��Ȥ@�_�Y�ȶ��C
�ߤW�b Surya Hotel �α��\�A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t�@���äH�̤l�йŪ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 (Rgyal bu don grub) �өM�ڭ̤@�_���\�A�L���Q�X�~�e�L��x�W�ɴ����L�ڡA�ڭˬO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o�F�C�]���e�@�ѱߤW�b�T���W�L�A�j�a�����I�֡A�ҥH����U�ۦ����𮧡C
�ĥ|��@���뢱����@�e�b�F�i�ĩԡA�ı߷f���^�w���f
�W�ȤK�I�ιL���\��A�ڭ̴N���V���]��z�h�СA�]���ڭ̷f�U�Ȥ��I���T���^�s�w���C�Q�I�Q���A���赦�����ͱa��ڭ̥h���[�L�ҥ�¾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ɮפ��m�Ϯ��]�v�A�ݤF���֬y�`�F�����öQ���áC
������ͯS�O�V�ڤ��Ф@�M�L�̹Ϯ��]�W�����áСm�����O�E�̯]���n(Bka' 'gyur, Phug brag edition)�A�o�O1959�~���ɬY�����N�u�����x�v���ê��o�M�øg�a�X�Ӫ���۪����A�o�Ӫ����öQ���a��b�]�t�F�ܤ֤Q�����b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Ҩ����쪺�ä�g��C�]���O��ۥ��A�ҥH�Ȧ��@���A�ڭ̥u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1706�~�H�e�K�s�b�C�Ĥ��@�F�����b�L���m�D�k���n(gsan yig) 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Ƴ��g��b�ؿ��W�L�ݨ�W�r�A���o���s��L�Ҭݨ쪺�U���øg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L�Ʊ榳�H�N�ӯ�����o�Ǹg��A���쪺�O�A�o�X�����@�F�ॼ���쪺�g��b�o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O�E�̯]���n���i�H���C�H�e�ڦb�Ϯ��]���j��½�L���赦�����ͤΨ�P�ƭ̩ҽs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̯]�����ؿ��A���S���`�N��䤤���S�O�B�A�g��O�߸����誾��öQ�C�٦n�o���øg�w�g�ѨH�a�����ͦb�ì��ҳп쪺�u�@�ɩv�Ь�s�|�v½�s���L�Y�v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C���ڨS�Q�쥦���쥻�O�o��j�@���A�ӥB�O�s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n�C
���ۤ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 (sman rtsis khang) �R�@�����ġA�ګh���K�R�F�@�ǥL�̩ҥX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C���ȩM������إ��ͦb Tibet Hotel �@�_�Y���A�P��|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Ѥ͡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
(Thog med) �C�z���O���Ю{�A�]�O�{�b�y�`�F��ij�|�����ХN���A��N�۷����W�C�o�@�\�����Q�X�ӤH�@�_�Y�A�۷����x�C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߬ݯf�A�ڭ̨�L�T�H�]�n�_�ХL�E�_�A�j�a��ı�o�ܷǡA�s
Su ���g�}�M�L�L���E�_�o�X�ӡC
����U�_�B�ӡA�ڭ̴N�^ Surya Hotel �𮧲�ѡA�ڤS�V���赦�����ͽбФF���֦��ê����v���D�A������ѡC�B����A�]�h�ѩ��S�R�F�X���ѡC�^�ӫ�A�j�a�N�b�\�U�Y�I���ѡA��Y���A�Ū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٧�L�����a�H�a�ӽФ��i���[���C
�ڭ̷f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^�s�w���A�^�{�����ȸ��h�A�ӥq���S¶����ȡA�ҥH�@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ӵΪA�C
�Ĥ���@���뢱����@�e�b�w����ơA�dzƫe���ԹF�J�f
���W�C�I����F���ç��� Zambhala Hotel�C�p��M�Z�ӳ�� (Dpal 'byor) �X�h�����ñ�һP�R�F��A Su �]���S���Φn�A���^�Х𮧡C
�کM���i���h�h�L�]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̡A��n��س�� (chos 'phel)
�]�b�C��س���O�ԹF�J�H�A�M���i���P���A�~���ɨ��^���x�Ǫk�A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ɦp�x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߫��ɤW�v�A�{�b�D�n�b���y���i��䥰�k�Ʒ~�C�b��w��̤l���٧U�U�A��س���b����X�ͦa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ؤF�@�y��μw����
Bauddha����٭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N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C
���i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H��F�@�U��p��A�N�@�_�U�ӫ��ɦ~������̮խ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A�ګh�]��ѩ��h�ݮѡC
���ȥѤp�⪺�w�ơA�ڭ̤@��H�Ь�س���� Hotel Intercontinental �h�Y�ۧU�\�A���O�a���P�Ū������A�ڭ̤]�����ɨ��@�U�A�Ȯɰk�s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Ѯ�C
����^�� Zambhala Hotel�A�]���Ѯ��b�Ӽ��A�j�a�����Q�ʡA�N�b�ж����B�dzƥh�ԹF�J�ҭn�a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ө������өM�ڭ̰ӰQ�ԹF�J����{�������Ʃy�A�L���S�̦��b�ԹF�J�A�L�]�Q�Ǧ����|���K�h���X�˱��C�����æ��@��[���j�y�����v�Х�������
(nyi ma sgrol ma) �ӦV���i���бШ�x�W����C���٪���T�A�o�{�b�b�k���Y�N���ߪ��u�Q�ٹϮ��]�v�u�@�C
�ߤW���I�T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Чڭ̨� Wangchen Hotel �Y�߶��A�Y���O�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C����^�Ӿ�z�F��A�M��j�a�����N��A�]���ڭ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_�ɡ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|�Q�����ԹF�J���Z���C
�Ĥ���@���뢱����@�e�]�ѭԤ��ΡA�G���w���ݤ@��f
���T�I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쩵�_���ɶ��A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ѡC����C�I�T�Q���A�~�����ŧG�]���ѭԤ��ΡA���Ѱ����A���䪺�P�����L�פp�j���Q�Ѥ]�����A�٦n��Ť��q���۫��٤����A���Ҧ��ȫȦ������Ǫ� Radisson Hotel�A�o�O���ꪺ�s�궺���A�]�ƺ��n���A�ڭ̥i�H�𮧤@�ѡC
���Ҧ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]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Ф���ɡA���w�g�֤Q�I�F�C���j�a�ެ~�L��A���i����ij�h���[�w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ëΡv(Tibet House)�C�u���ëΡv���۷���y�`�F���]��Y�Ǥ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ä�Ƥ��ߡA�Ӧ��w�����o�ҬO�䤤���v�̱y�[���C��F���̡A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C�ȡA�ڭ��H�����[��U�h�A���媫�i�⤤�ߡB�ժ��]�B�H�ιϮ��]���A�ڶR�F�⥻�L�̩ҥX�����ä���y�C�]���Ѯ��b�Ӽ��A�ڭ̫ݤF�j���@�Ӥp�ɡA�N���D�^���]�j�N��h�A���\�Y���O��Ť��q�۫ݪ��ۧU�\�C
�U�ȧڭ̦U�ۦb�Ф��𮧡A�]���کM���i���P�@�ж��A���ۨS�ơA���i���N��ڭ�R���Ѯ��ӬݬݡC�Ĥ@���O�Q�C�@���线���_�� (byang gter) �ǩӯ��v�����h��
(Dbang drag rdo rje) ���۶ǻP�ۧ@�A���i����_�öǩӫܼ��x�A���L�]�S�ݹL�o���ѡC�ĤG���ѬOı�n�����v�^���ج� (Kun dga' grol mchog,
1507-1573/4) ���۶ǡA�o���Ѧ]���H�e�g�פ�ɥιL�A�ӧ@�̤S�O�ڷ��P���쪺���v�H���A�ҥH�ݨ�o���Ѥ@�w�n�R�C���i���b½�\�o���Ѯɧ�줣�֦��Ϊ���ơA�Ҧp�^���ج�b�ԭz��e�ͨ��ݮɡA�O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ڵ��E�F������
('bar rom Dar ma dbang phyug) �P�sĶ�v (Gnyos Lo tsa ba)�A�e�̬O�ڵ����|���l���A�ӫ�̫h�O��^���|�쯪�N�ѧ������D�n�̤l���@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H���ǰO��ƥ��ӴN���h�A���^���ج�b�s�g�o�ǶǰO�ɡA�ͨ�L�O�ѦҡB���H�e���ǰO�Ҽg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ӴN�b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ǩӪ����v��ơA�ҥH�ݨ�o���Ѭ۷������A�U�Ȫ�F�j���T�p�ɦb½�\���ѡA�ݨ즳�쪺�a���٤��R����ť�A���F�ڤ��֨��ѡA�]�`�٧ڤ@�ǥH��d�\���Ѫ��ɶ��C�ҥH�کM���i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ڬO�w�P��o�⥻�Ѥ��i���|�αo��A�ҥH�~�R���C
���\�N�b���]���\�U�ο��A���M�٬O��Ť��q�۫ݪ��A����ڭ̴����N��A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Q�����n�_�ɡA�~�����ԹF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C
�ĤC��@���뢱����@�e��ԹF�J�A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ګݡf
���I�|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שQ�_���A�q���f��h�A���D�U���L���A�o�]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ӡA�ݱ���ԹF�J�ϰ쪺�ߺ��Զ��s�ߥ_�ݮɡA�s���л\�M�s�A�ݨӫe��骺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p�C
�Ө�ԹF�J�¸t�A������ԹF�J�����v�I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A�ѡA���M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S���C�ԹF�J (La dwags) �o�Ӧa�W�O���ä�W�r�A�Ԫ��N��O�s�A�ԹF�J���N��O�u½�s�v���N��A���O�o�ӦW�r�X�{�a���O�Ӧ��A�j���O�Q���B�Q���@���ɤ観�C�H�e�äH�٩I�o�Ӧa��s�u����v(mar
yul, �C�a)�A�O�ҿת��u�����T��v(mnga�� ris skor gsum)
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C�o�Ӱϰ������ä�ƪ��v�T�A�O�Q�@���~�}�l���Ʊ��A�ӧڭ̹蠟�e���ԹF�J�j�N�v�A�٬O���ܦh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a��C
�Ө�ԹF�J���̦��H�ءA�����O�ҿת� Dardi �H�A�ݩ��Ӧۤ��Ȫ��L�סХ�ԥ��� (Indo-Iranian) ���@��A�o�ӥ��ڪ��ܤ��餴�D�n�ͦs��ԹF�J�n��
(�L�̲{�b�٩I�ۤv�� Maknopa)�C�H���Ǯa��{���ԹF�J�a�ϥ��ڲV�X���Ϊ���s��ܳo�̪��H�إD�n�ODardi �H�P���äH���V�X�H�ءC�b��þ�H�J�I��_�L�إ��Ԫ�ù���� (Gandhara)�ɡA��þ����m�w�g������
Dardikai �H���O���A�o���ܥL�̤j���b�褸�e�G�B�T�@���ɤw�g�Ө�o�Ӧa�ϡC�b�P�����m�̡A�ڭ̤]�ݨ�ҿפ��Ȧa�Ϧ��|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ƪ��O���A�o�q�ǻ��b���v�W�۷����W�A���Ǫ̫��X�o�q�ǻ������
Dardi �H�b�ԹF�J�P�ڴ����Z (Baltistan)[4]
�a�ϫ����q���ҽk�O�СF�o�Ӧa�ϩ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b���v�W�۷��ۦW�A�o�i�H�Ѻ~��v�Ƨ���ҾڡC
�Ѧb�ԹF�J�ҵo�{���j�Ѧ��c�� (Karosthi) �O��j���i�ҩ��o�Ӧa�Ϧb�褸��B�G�@���ɬO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ª��Ϊv�A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o�q�ɴ�����ƹ�b�ӹL���q�A�ڭ̵L�k�o�����ɪ���ڪ��p�A���O�ѥ�������Ԫ�ù����P�Q�����ª��Ϊv�ӬݡA��жǤJ���@�a�����Ӭ۷����C
�b����v�Ƹ̡A�o�Ӱϰ�ܦ��N���O���A�k�� (337-422) ���m���O�n�٦����u�Ťe�v�A���L�S�ӹL�o�a��C�k��H�����ʦ~�A�ȮN�Ѧ��g�{�����ڰZ�i�J�_�L�סA�ھڥL���m�j����O�n�A�q�_�L�ת��u�}�S�h��v(���L��
Kulu) �V�_���A�g�u���@ù��v(���L�� Lahul)
�A�V�_���A�N��u���ޮP��v�A����S�١u�T�i�F��v�A�i�O�ȮN��u���@ù��v�P�u���ޮP��v���O�z�A�D�O�ھڶǻD�ӨӡA�L�ۤv�]�S�h�L�C�Ǭɤ@�뤽�{�u���ޮP��v�N�O�{�b���ԹF�J�a�ϡA���O�o�ӦW�r���ӷ��o�ᦳ��ij�F���H�{���o�O��Ķ�ä媺�u�����ġv
(Mar sa, �]�O�C�a���N��A�O�ԹF�J�j�W�u����v���P�q��)�A���O�o�ӻ��k�{�b�ݨӫܦ����D�A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ڭ̭n�ӻ{�b�褸�C�@�����ɭԡA�ԹF�J�w�g�b�y���ä�F�A�o���G�O���ӥi��ơA�䦸�A�ȮN�b�m�j����O�n���A��L�צW�r����Ķ�O�ܳW�ߪ��A�q�����Ρu�ޡv�r����Ķ
ra �o�ӭ������ΡC�ȮN�b�Ѥ�����L�u����v(Suvarnagotra)�A�O�b�u�j�ϦP��v���ϰ�A�U�W��q�A���겱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u�j�ϦP�v�N�O���þ��v�����賡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v(zhang zhung) ����A�]�O�ǻ������Ъ��o���a�C�b���ת��ä���v���m���O���A�褸719�~�ɡA���ù�u�����v�P�u���v(mar)
���F�H�f�լd�F���Ъ����v���m�`�`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v(zhang zhung
smar)�A�o�W���b���פ��m���]�X�{�L�⦸�A��ܡu�����v�P�u���v�o��Ӧa�観�۷������p�C�i�@�B����s�o�{�A�b�{�����ЩҫO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r�J���Asmar �o�Ӧr���N��N�O�����A�]���ڭ̤j���i�H�q�o�Ǹ�ƧP�_�G1. �ԹF�J���j�W�u����v�M�C�a�L���A�ӻ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2.
�ȮN�Һ٪��u���ޮP��v�A�o�ӦW�r�����Ӧ۷��ɪ������y�A�ӫD�ûy�C3. �o�Ӧa�ϩM�ȮN�Һ٪��u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O�j�ɡu�����v�a�� (�Ρu�j�ϦP�v) 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C
�b���ä�ƥ��v�T���a�ϥH�e�A�o�̪���ХD�n�O�q�ؤ��̺����̿�J���A�o�i�H�q�{���ҿ�d���@�ǤK�@�����k�ɴ����O��P�ݥX�ӡC
�ԹF�J���M�b�C�@���ɴ��g�ǤJ�Q�٩����ҫإߪ��R���Ұꪩ�ϡA���H�۫Ұ�դO���I�h�A�F�v�W�å��u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ϰ�C����ԹF���� (glang dar ma,
?-842) �Q����A�L���j���m���l�x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áA�p���m���l�h�Q�����A�k��ԹF�J�A�b�a��Q�ڪ�����U�A�إߤF����C��N�H��A�Ǧ�ܩu�w�����O (skyid lde nyi
ma mgon, ��975-1000�b��)�A�L�N��g���ʵ��T�Ө�l�A���l����N�~�ӤF�ԹF�J������A�Φ��F�ԹF�J���Ĥ@�Ӥ��¡Сu�Ԥd�v����
(lha chen)�C
�u�Ԥd�v���©M���ɪ����ä@��A�]��P�O���Ъ��ɤJ�P�����A�Ҧp���æ�Ыᥰ�����jĶ�v���ܮ�i
(Rin chen bzang po, 958-1055) 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O�P��l�ڦN�O (Dpal kyi mgon)
�b��ɡA��ԹF�J�a�Ͽ��ؤF�@�ʹs�K�y��Цx�|�A�ܤ����M�j�����w�g���s�b�F�A�ڭ̤��M�i�H�b�ԹF�J���@�ǿ��A���O�u����ɦp�x�v(�{�ݤ�^���|) �P�u���O�x�v(A
lci, �{�ݮ�|��) ���x�|�A�H�μƳB�ݦs���٧Q��C
��^���|�P�ԹF�J���«ܦ��N�إߤF���Y�A�b�N�ѧ����C�Q�T�����ɭ� (1215)�A�L�����̤l�j������ (Gu ya
sgang pa) �쩣�����s�إߦx�|�A���ɪ��ԹF�J���ЩԤd�o���O (Lha chen mngos
grub mgon) �N�O�L���I�D���@�A�q����^���|�b�ԹF�J�إߤF�Ь��դO�C�P�ɡA�i��O�b��^���|���v�T�U�A�ԹF�J����ЧΦ��F�s�ǹ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ïd�Ǫ��DzΡA�o�˪��Dzι�ԹF�J���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T�A�ϱo���ëO���b��Q��ƤW���u�աA�ñN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Ԫ���K�C
�Q���@���ɡA�ѩ�v�ؤ� (1357-1419) �ҷs�خ�|�����v�T�A���ɪ��ԹF�J���Х����w (Grags
��bum sde) �N�@�y�ة�Q�@�@�����j�x�Сu���g�x�v(Dpe
thub) �e����|���A�v�ؤڪ��@��ԹF�J�̤l���·S��i (Shes
rab bzang po) �إߤF�u�j�ҩԱd�v(stag mo lha khang)�A���·S��i�����l�·S���� (Shes rab grags pa) �b��ǫإߤF�u����x�v(Khrig se) �A�o�Y�O�{���ԹF�J��|���̰��줯�i���Фڮw�Ԥ��i�� (Bakula)
���Ҧb�x�|�C
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̧̦W�s���ڥ� (Grags pa ��bum)�A�Ǩ�]�l�W�s�Ԥd�ڰ� (Lha chen Bhagan)�F�����w�N����Ǥ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(Blo gros mchog ldan)�A���H��Ԥd�ڰ��Y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½�A�إ߷s�����¡A�o�]�N�O�ԹF�J���v�W���ĤG�Ӥ��¡Сu�n�šv����
(Rnam rgyal)�C�Ӥ�^���|�]�b���ɭ��s�M�s���«إߤF���Y�C
�Ԥd�ڰ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n�� (Bkra shis rnam rgyal, ��1555-1575�b��) �O�@��۷��j�ժ�����A�L���פF�Ӧۤg�ը䪺�դO�J�I�A���X�i�ԹF�J����a�F�t�@�譱�A�L��Ф�^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^������
(Ldan ma Kun dga�� grags pa)�A�^���W�v�A����إߤF�u�����x�v�A�äS�N�]�A�u����ɦp�x�v�b�����\�h��a�絹�L�z�A�o�O��^���|�Ь��դO�b�ԹF�J�ĤG���_���C�]�O�b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ɭԡA�ߤU�C�Ӯa�x�ܤ֦��@��k�ĥ����X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x�C
�U�@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n�� (Tshe dbang rnam rgyal, ��1575-1595�b��) �A�L�j���O�ԹF�J���v�W�̵���Ԫ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F�L����F���æ賡������
(Ngan rings)�B�j�� (Gu ge)�B���� (Pu rangs)
���a�F���n����F�{���� Kulu �P Jumla�F����i��^�жդO���ڴ����Z�a�ϡA���\���X�i��g�A�åB���F�ӷ~��q�A�j�O���عD���B���١A�i�H���n�Ť��¦b�L���Ϊv�U���w�F��¦�C
��F�����n�� (��Jam dbyangs rnam
rgyal, ��1595-1616�b��) ���ɭԡA�L�]�����J�_�� Purig
���Ԫ��A�ϳQ�ڴ����Z���^�Эx�������ѫR���A�ϩԹF�J����оD����D�`�j���}�a�C�ڴ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j�G�L����k���d�A��ͤU�@�l�F�ڴ����Z�P�ԹF�J�p�áA�O���F�Ϧ^�жդO�i�J�ԹF�J�A���O�b�o�����^��ԹF�J�H��A�L�ߦ~�o�O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v�СA�P�O��ԹF�J��Ъ����ءA�ÿ˦۰Ѥ��sġ�g��C
�����n�ŻP�ڴ����Z���^�Ф��D (Rgyal Khatun, �ԹF�J�H�{���o�O�իץ����ƨ�)
�ҥͤl�Y�O����n�� (Seng ge rnam rgyal, 1616-1642)�A�L�O�ԹF�J���v�W�̨��H�R�q������C�b�F�v�W�A�L�P�ڴ����Z�@�ԡA���\���_�F���˥�������
Purig�F�t�@�譱�A���A�F�F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 (Gu ge)�A�H�ήᴵ�� (Zangs dkar) �a�ϡF�P�ɡA�S���פF�Ӧ۽��æa���äڦ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O�s�F�ԹF�J���W�ߦa��C�b�v�ФW�A�̥D�n���N�O��ШӦۦ��ê��ˤھ��|���N�̹F�ܤ��
(Stag tshang ras pa,
1574-1651) �C����F�ܤ�ڡA�b�ԹF�J�y�Ǧ��o�˪��G�ơG������n�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Ū�Х����E�^�����ڨ�ԹF�J�ɡA�L�Q�гo���^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N�̧@���ԹF�J���Ǫ��W�v�A�^�����کڵ��F�A���L�w�����G�u�N�ӧA�|���@��W���u��l�v���l�]�A���@��W�s�u�Ѫ�v���ˤھ��|���N�̷|�Ө�ԹF�J�A�]�����۩M�A�L�̷|�����v�{���Y�C�v����n�Ū��u����v�ä�N��N�O��l�A�ӹF�ܤ�ڪ��u�F�v�N�O�Ѫ�C�b����n�Ū�����U�A�F�ܤ�ګإߤF�u�¦̦x�v(He
mis)�A�����ȬO�{���ˤھ��|�b�ԹF�J�̤j�B�̭��n���x�|�A�]�O�ԹF�J���Ǫ��x�|�F�F�ܤ�ڤ]���U����n�ũ�1623�~�b�u�¦x�v(Shel) �سy�@�y�T�h�Ӱ������ǦA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n�šA�o�y�{�����O�s���n�C�F�ܤ�ڹ�ԹF�J��Ъ��v�T�O�۷��`�����A�ѩ�L���P�l�A�ˤھ��|���ȱq�������ԹF�J���̤j�դO���Ь��A�L���W�v�Щ~����ê��i�z���i��
(Yongs ��dzin) �ǩӤ]�����ԹF�J���ǥû����W�v
(dbu bla)�C�t�@�譱�A�ѩ�F�ܤ�ڪ��}���@���A�H�ΩԹF�J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ӥ@�U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Y�A�ˤھ��|���M�b�ԹF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Ǫ��H�^�Ь��A���U�ӱЬ����o�i���ܧ��šB�M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ˤھ��|�F���Ϋ�Ӧ��ê���|���F���@��A�]���ѹ��H�Ϊv�A�y���Y�@�Ь����W�j�C
����n�Ť��᪺�ԹF�J���v�A���O���b���ê���|���F���P�L�ת��^�лX�a����� (Moghul) ���D�s���İ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÷s�إ߮�|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x�ƫI���A�E�V�X�a����½ЧL�ϴ��A�^�Эx�����U�ԹF�J���h�F���áA���O�H��N�}�X�F����G�ԹF�J���w�ǫn��
(Bde legs rnam rgyal, ��1680-1691�b��) ����H�^�СB�V�ؤ��̺��ǰ^�B�b�ԹF�J�����^�е��A�ɭP�q���ԹF�J���v�D�v�N���J�^�Ъ��X�a����¤⤤�A����Q�K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a����®�������C
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F�����ìF���A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N���ܩԹF�J�i�}�ͧP�A�ԹF�J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ê���ơB�ӷ~���Y�U�A�S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H��СB���w��ɡB�ǰ^������A�q�Өϱo�ԹF�J�ॢ�F�F�����j�q��g�C
��Q�E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e�A�ԹF�J�@���B��o�ا��_���ͦs�A���M�p���A����_�ӡA�ԹF�J���g�ٵo�i���۷��I�ΡC��F1834�~8��A��� (Janmu) �����J�Ф���A�b�N�x Zorawar ���a��U�A�vDogra�x������ԹF�J����A���Цx�|�y���F���j�l�`�F���J�Эx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@�B�i����áA�]�J�j�����ӥ��ѡC1842�~�A���J�Ф���P���íq�����M�A���ĻP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ӷ~��q�S�A��_�A���ԹF�J�w�g�����ǤJ���J�Ф��ꪺ�Ϊv�A�]�N�O���A�n�Ť��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n��
(Tshe dpal don grub rnam rgyal, 1802-1840�b��) �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M����Ǯa�ڤ�����ܤ��C
1846�~�A���J�а���P�^�ݦL�F��ñ�q��w�A�����ؤ��̺����Ϊv�̡A�ԹF�J�]�]���ǤJ�䳡���C�o�˥b�W�ߪ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1947�~�A�L�P�ڰZ�����^��Ϊv�U�ۿW�ߡA�ѩ�L�ױлP�^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Y�A�i�}�F����ܤ������ؤ��̺����ɪ��G1954�~�A�ؤ��̺��֤J�L�צ����@�١A�ԹF�J�]�]���k�J�L�סA���L�P�ڰZ�����ؤ��̺��Үi�}���ɪ��A�b1965�~�B1971�~���O�}�ԹL�A��{�b�٨S���ѨM�A�ҥH�]�y���ԹF�J�b�a�z��m�W���ӷP�C����1974�~�A�L�㤩�ԹF�J�}���[���A�o�]�O�ԹF�J����g�٦��J���D�n�ӷ����@�C
����ԹF�J����СA�p�e�ҭz�A�D�n�N�O�H�ˤھ��|�B��^���|�B�H�ή�|���T�j�Ь����D�A�ĭ{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x�|�Сu�����x�v(Ma spro)�A�线���H�e�]�u���@���u���j�x�v(Brag stag)�A��~�s�ؤ@�ҡC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N�b�ԹF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v�ä����A�D�n�O�b�n�Ť��·��`��A�����ìF���v�T�ҭP�C
�ڭ̪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I����F�ԹF�J�����C�� (Leh) ���ߤ@�����A�o������ڤW�O�ӭx�ξ����C�ԹF�J���a�z��m�A�F��L�סB�ڰZ�B���I���B�H�Τ���sæ����ɡA�ѩ��N�L�P�ڰZ��ؤ��̺����D�v��ij�ҤޥX���ɤO�A�t�~��911�ƥ�H�ӳ�Ϫ��I����߯Z�F�v�Ԫ����v�T�A�ҥH�@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B�i�����j��u���x�H�C���b�s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i����x�Hĵ�١A�]���ڭ̨�L�ת��o�q�����A��n�S�I�W�j�ηS�S��
(Gujarat) �L�ױЮ{�P�^�Ю{�쪧�ܸt�a�Ҥް_���Y���ɶáA�ҥH�����ٳƯS�O���Y�C
�~��i�J��ů��A�N����Q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b�����ۡA�ڭ̤T��̤l�g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W�]�h�F�n�h�����F�CSu �P�p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D�ԹF�J�|�N�A���S���ƨ�a�ճo�ASu 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A�p��h�O�@�U�����N�}�l�Y�h���ΪA�F�ڭˬO�٦n�A���Ӿ�߷|�����s�g�����A�U������u�yı�o��ݡA�䥦�˳��S����Pı�C�@��H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Ө�u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v(Hotel
Lumbini)�A�o�O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ӤөҶ}���A�ڭ̱��U�ӳo�X�ѳ��N���b�o�̡C��F��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w�b���f���ۧڭ̤F�C
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O���a��^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S�A�⦳�u��ǡv(chos rje, �k�D�Ϊk�L���q)
���Y�ΡC�Ĥ@�@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O��^���|�ĤQ�C�N�k�����ܩb�� (Rin chen
phun tshogs, 1509-1557) ���̤l�A�X�ͩ�^�i�a��
(Kong po)�A�M�ԹF�J�S�����Y�C�ƹ�W�A�e���@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O�b�d�æa�Ϭ��ʡA�q����賡�a�϶Ǫk�C����Ĥ��@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z�
(bstan 'dzin chos grags)�A�X�ͩ���æa�ϡA�Q�ܽШ�ԹF�J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^�Ŧx�v(phyi dbang sgang
sngon dgon pa) 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æ�������ԹF�J���е����n��
(Tshe dbang rnam rgyal, ��1760-1783�b��) �P�����n�� (tshe brtan rnam
rgyal, ��1783-1802�b��) ���W�v�A�i�H���]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Y�A��^���|�P�n�Ť��¤��Ǫ����Y���s�F��F����C�L�ߦ~�^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龿�x�v(yang
ri sgar) 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æb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ɡA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|�Ь�����F�C
�ĤC�@����@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ǩ��� (Ngag dbang dge legs dbang phyug)�A��X�ͩ���áA�^��u�����^�Ŧx�v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N���^���n�� ('Jigs med kun dga' rnam rgyal)
���W�v�A��1830�~�_�A��H�@�P�����ԹF�J����F���C�o�줣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b�ԹF�J�Q���J�Ф��ꪺDogra �x�����ѫ�A�k��^���ݦa�A��1835�~�L�@�C���i���h�e���L�״¸t�A��ҭ}
(Mandi) 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A�~�G�Q���C
�ĤK�@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P�ԹF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̬��K���A�L�N�O�e�z�ԹF�J���l����l�A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Ű� (Ngag dbang blo gros rgyal
mtshan)�A�^��u���龿�x�v���پDzߡA�����@��ۦW���Ǫ̡C�b��^�ԹF�J��A�L���פF�u�����^�Ŧx�v�P�u����ɦp�x�v(Bla ma g.yu ru)�C
�ĤE�@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X�ͩ�ԹF�J�_�����@�a�H�a���A�^���^�DzߡA�L��j�¼w���誺�����N�b���ɬ۷����W�C�ڹ�L���ͥ��Ҫ��|�֡A���b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Ф�����L�L�e�@���Ӥ��C
�{�b�ĤQ�@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1939�~�ͩ�ԹF�J�_�����ߺ��Զ��s�ϡA�Q�|���ɦ^��u���龿�x�v�DzߡA1959�~���@�J�ë�A���i���^��ԹF�J�A�~���ɤ�^���|�U�x�|�b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ǩӡC1998�~�A���i���Q�אּ�ؤ��̺��٪��u�ԹF�J�ݤ��@�ưȧ����v(Minister
of Ladakh and Public Affairs)�A�]�N�O�ԹF�J�a�Ϫ��̰���F���x�A�����줵�~�K�묰��C
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M���i����F�@�|�A�]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Ŧ���Ӧn�A�]���I���s�g�����A�N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n�n�𮧤@�U�C�Q�@�I���ɭԡA���i���s�کM�L�@�_�h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a�̧䤯�i����ѡA�� Su �P�p��n�n�𮧤@�U�C���Ȥj�a�@�_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U�Y���A�Y���O�ԹF�J�a�護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C
�U�Ȥ��i���a�ڭ̥X�h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W�ӥj�ݡA�]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ԹF�J��F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Y�A�ڭ̥X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᳣���x���ɤ��@�áA���M�{�b�٥���ȹC�u�`�A���W���O�ܼ��x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I�S�ӹL�A�]��ޤH���ءC
�ڭ̥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y�۷��j���٧Q����[�A�o�O�Q�X�~�e�Ѥ饻�齬�v���k�x�Ү��ت��A���M�O���ü˦��A�����a�H�U�١u�饻��v�C��b�b�s�A��n�i�H������ӦC���A����ᬰ�u���C�𰼦��@�馡�p�q�A���L�饻���H�A�Ȧ��@�ѳ���ݺޡC�ڭ̶i�h§��ɡA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٫ܦ���a�۰_��媺�u�n�L���k���ظg�v�A���O����}���ɥLť�饻���H�ۻw�ɩҾǪ��C
�H��i���a�ڭ̨�C���t�@�Y�s�y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h���[�A���c�W���u�j�C�N���c�v(Gle chen dpal mkhar)�A�o�O�ԹF�J���v�W���^�D�й���n�ũҫسy���A��Ӱ��E�h�A�{�b���M�h�w�}�ѡA�����i�Q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e�A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ĥ��F�Ԯc���˦��N�O�ѦҦ��c�ӫءC���c���æ����Ī����̯]���A���Ī��ä��O�ܦѪ������A�i��]����b�o�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v�T�A�ݰ_�ӫ��¡C�o�Ӥ��c��ꤣ�p�A���O�]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I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દ�W���U���Ӧh�ӱ�A�ҥH�ڭ̤j���ݤF�G�Q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F�C
���ۦ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Чڭ̨�L����c���@���A�]�N�O�L���p�H�x�| (Rtogs ldan pho brang)�A�]�����o�Ӥ@���A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ȦY���ɽЦ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ڭ̴X��x�W�̤l�ݬݥL�Ҭ��ê��v���_���A�ҥH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S�a�a�ڭ̹L�ӬݬݡC
�o�y��c�ٺ�ܷs�A�]�A���j�p���T�B�A�H�Τ��i���ۤv�����a�B�ϮѫǡA�F������1998�~���Ӧ��}���A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ٱN���ɹ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ж���ʤ��ʪ��O�s�U�ӡC���ۤ��i����ڭ̨�@���p�ж��A��̤ͪ�}�A�M�ᥴ�}���ΤU�w�g�W�ꪺ�d�l�A�@�@�i�ܨ䦬�áA�u���}�F���ֲ��ɡC�䤤�@�ǭ��n���O���p�U�G
1.
���{�ȥ���٧Q�G�o�O���i���Ѥ�^���x�ұa�X�Ӫ��٧Q�l�A��b�@�Ӥp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٧Q�𤤡A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ۤv�]�n�[�S�����}�ݹL�A�o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ڭ̬ݡA���M�S�ͥX�F�\�h�j�j�p�p���٧Q�l�A�����٪��ۦb�����W�A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D�`�����A�ڭ̤]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F�@�I�C
2.
��ǪL�� (Chos rje
gling pa) 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G�o�O�L�Ҩ��X�����áC
3.
���s�E�ڦN�h�� (Lha lung dpal kyi rdo
rje) �����ڪS�G�L�Y�O�åv������}�a��k���ä��Թ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٫U���H�C
4.
��^���|�ĤT�Q�@�N�k�����^�E�ϳǥ��� (Skyabs mgon Thugs rje nyi ma, 1828-1881) �ҧ@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ڪS�C
5.
���j���j�¼w����S�G�o�O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~�k�X���îɦۤ�^���x�ұa�X�Ӫ��C
6.
��^���|�ĤG�Q���N�k����z� (Rig ��dzin chos grags, 1595-1659) �ҧ@����ץ��G�L�ۧ@���סA���DZ¤j�¼w���褩�Ĥ��@�F�����C
7.
��z���ø���j�¼w�����d�G�o�T���`�öQ����d�A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餣�H�K���X�ӵ��O�H�ݡA���Ѧ]���Դܤ��i���O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n�ͤ��G�A�ڭ̤~�g���o���C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e�@�O�@��M�פj�¼w���誺���N�̡A���L�b��^�u���龿�x�v�Dz߮ɡA�ĤT�Q�T�N�k���«¬��� (Zhi wa��i blo gros, 1886-1943) �N�o�T��z���ø����d�ػP�L�A�]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H�Y�O�j�¼w���誺���N��
(��^���|���j�¼w����ǩӧY�O�ѥL�ҶǤU)�A�k���é��d�I���ˮѯ���A�\�W��L�C����d���e���ݡu�´ܬ��v(Mkhyen
rnying lugs)�A���M��^���x����d�j�����ݦ����椧�e���A���o���¬�����d�{�b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C
8.
�Ӧ۹F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ڪS�G�o�]�O���i���ۦ��ña�X�Ӫ��C
9.
�¥��Y�W���ѵM���զ�u���v�r�A�H�ΥեۤW������L�G�o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Y�줯�i�����~�ҧ@���@�Ӧ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ê��ڡA�b�L���ӫ�N�۵M�\�b����A���~��ť�Դܤ��i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ơA����ש�ਣ��C�����Ӥ��i����J�A���ƸԱ����ऽ�}�C
10.
�եۤ���ץ��G�o�O���i���Ҩ��X�����ä��@�C
11.
���E��B�ڪ����ئG�L�O�N�ѧ������D�n�̤l���@�A�]�N�O�{�b���d���i����@�ǩӪ��Ĥ@�@�C
12.
�ĤT�Q�T�N�k���«¬����ҧ@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C
�ܷP�¤��i���D�`���@�ߪ��N����ä@�@�i�ܵ��ڭ̬ݡA�\�h�F�褣�ȬO�j���A�b�v�ФW�A�S�O�O��^���|�ǩӪ����v�W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A���H�Ǧ��o�H�l�з��~�o�Ǧ��N�̪���ˡC
�ߤW�b���]�ɥιL�ײ������\��A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A�]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A�[�W��찪�a�A�٬O�n�n�n���i��O�dzƱ��U�ӴX�Ѫ��ѳX�C
 |
 (����) �G�Q�|�N�k����z��ҿ�ø���j�¼w�����d�A��I���W�� (�k��) �O�ĤG�Q�E�N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ź٪���L�A�U��h�O�T�Q�N�k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٪���L�C�h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áC |
[1] ���夤�ҥΪ��ä�ù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D�H�dzN�ɳq�Ϊ��ä�u���O�v���k (Wylie Transliteration)�C�@��a�W���D�u�β{���L�P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ߺD���k�A�Y�D���n�A�����٭즨����W�C
[2] ¤��D�M�N������a�W�A�æW Nyag rong �A�{���|�t�٥̧��ñڦ۪v�{�s�s���C
[3] 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^�i�h�y�ѥ[���~��§�ɡAGene Smith���ͧi�D�ڥL���u���æ�и귽���ߡv�w�g�N�o�@�M�ѱ��y�J�q�����F�C
[4]�Y�~��j�y�����u�j�k�ߡv��A�ݤ��ڰZ�F�_�a�ϡA��`�����ä�Ƽv�T�A���餴�i�����C